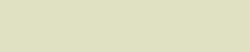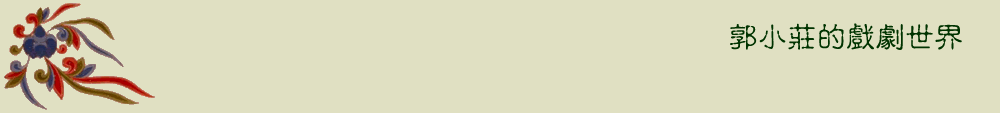
西方人的「國劇」觀 中國戲劇的舞台藝術,受到西方人士的重視,一般人全認為是由於梅蘭芳在民國十九年訪美演出的成功。實際上,梅氏訪美演出,雖則獲致觀眾廣泛歡迎,並且接受了美國波摩那大學Pomona College的名譽博士學位,但對西方劇場的影響,並不十分顯著。可以說,梅氏訪美演出的成功,是屬於他個人的,自文化傳播角度來看,不及他於民國二十四年第二次出國訪歐演出的具有文化意義。這並不意味著梅氏在相距六年之間,技藝上有若何顯著的進步,而是他訪歐演出,不僅再度顯示他個人的技藝,主要的還是中國舞台藝術,因而導致國際性權威戲劇家的公允評價,進而影響西方劇場。 梅氏訪歐演出,觀眾中包括歐洲第一流戲劇家多人,如藝術劇院創始人丹欽柯N. Danchenko,電影藝術家愛森斯坦 Sergei Eisenstien,詩人兼名劇作家白烈克Bertolt Brecht等人。他們通過梅氏的演技,認識了中國舞台藝術的整體性戲劇功能,一致肯定中國劇場的絕對價值。 綜合他們的意見,不外由兩個基點出發。 (一)中國戲劇合乎「舞台經濟」原則,這是丹欽柯給予中國舞台藝術的總評。他的意思是指中國舞台的時空處理之自由性,以及服裝,道具等的目的性與統一性。這是西方倡導「整體劇場」Total Theatre的先聲。 (二)演員表現能力的優越:白烈克追記他在劇場接應室中會見梅氏,梅氏穿著西方禮服,向他解釋中國戲劇特質的神情姿態,使他感覺西方舞台演員表現力之貧乏無能。這就是此後西方劇作家高呼「戲劇應回到演員身上去」,以及重視中國演員的長期接受嚴格訓練方式的原因。 中國戲劇,自十八世紀以來,一向被西方人士所曲解,甚至認為是野蠻而幼稚的劇場,經由這些戲劇權威人士的慧眼卓識,撥雲見日,指出中國舞台藝術的真諦,西方人士才逐漸擺棄錯誤的局限觀念而加以正視。 這其間,也有另一因素,促進西方人士對中國舞台藝術的傾服。二十世紀二、三十年代,正屬西洋藝術思潮,努力揚棄物質世界的種種束縛,轉向超現實方向邁進的時期。東方劇場藝術的象徵性表現手法,著重於內在精神世界的浮現,對一向以寫實為主流的西方劇場,不啻是「當頭棒喝」。印尼巴利島的舞劇(Dali danie),經由法國名劇作家阿托特Antonin Artaud的推崇介紹,震撼了歐美劇場。日本的能劇Noh和歌舞伎Kabuki,也由歐美及日本的戲劇學者陸續推薦,見重於世。同屬東方劇場藝術系統的中國國劇,巴利舞劇,和日本的能劇和歌舞劇,以不同的風格,展示於西方劇場,這股衝擊力量匯成一股潮流,使他們感覺到吸收外來影響(Alien Effect)的重要。 梅氏訪歐演出,距今已有四十年,這段期間中,曾有熊式一先生的英譯「王寶釧」。英籍旅美戲劇家士高特Al Scott英譯「蝴蝶夢」。楊時彭先生英譯「烏龍院」,都獲致相當成功。還有劇團的出國演出,西方接觸中國戲劇的機會越來越多,了解的程度也越來越深。泛覽他們有關國劇的論述,真有好些精闢之見,值得介紹給國人,試分六項,綜述於下。本文取材方面,以美國莎菲亞.特兒薩女士(Sophia Delza)所寫的「中西古典劇場」The Classic Chinese Theatre」文居多。特兒薩女士是位現代舞者,曾旅居上海兩年。由於熱愛中國戲劇,曾延請大舞台的一位演員,教授國劇舞台動作,同時另從一位老師學習吳派太極拳。雖則她並不是一位戲劇家或戲評家,但她對國劇的知識頗為深厚,視野很廣,見地也很真實。 一、劇場的大眾性 國劇來自民間,植根於民眾。中國人喜愛戲劇,戲劇是中國人生活的原動力。民眾根據生活經驗,為自己創造戲劇,娛樂自己。舞台藝術反映觀眾,同時也服務觀眾。 中國民眾經過一個很長的時期,在村落的「廣場」上看戲,隨後在「看棚」裏看戲,在「茶園」裏看戲,現在在戲院裏看戲,仍然一面看戲,一面喝茶。(按所指為大陸時代的戲院情況,下同)。從表面看,中國觀眾好像不如西方觀眾在看戲時那麼聚精會神,劇院裏常有很多干擾現象,茶房來沏茶添水,販賣冷熱食的穿來走去,孫子們在走道上模倣演員的動作,還有觀眾無休止的喁喁閒談。但是,無論如何,觀眾的眼光永遠集中焦點於舞台。雖有談話聲,觀眾對台上總有適度的反應表示,到時而大聲叫好,或是表示不同意的喝到采,舞台和觀眾總是打成一片,觀眾也成為戲劇最後的批判者。 鄉村演戲更富於民眾趣味,觀眾扶老攜幼,成群結伴而來,坐著,站著,甚至躺在樹蔭下看。婦人們做女紅,老者吸煙,幼者吃零食,做遊戲,仍都在欣賞演出。戲劇也同時傳授他們以興味性的歷史故事,神話故事,中國兒童沒有一個不知道「關公」,有如美國兒童無不知道華盛頓的,戲劇代替了鄉村教育。 西方劇場的觀眾是正襟危「坐」,屏息靜氣的注意傾聽台詞,一句也不能漏過。東方劇場的觀眾是「生活」於劇場,儘可隨隨便便,有意無意的看戲,而後者實較前者為接近戲劇的原始意義。西方戲劇工作者,近來提倡街頭戲,顯然受到東方劇場的影響。 二、演員是舞台的主宰者 中國戲劇的結構,不像西方戲劇的注重『懸宕』Suspense,觀眾早已洞悉劇情。劇情也是屬於直線開展式,而非曲折發展式的,這種戲劇結構,台詞並非最主要成份。戲劇表演最高潮處,往往不借重於台詞的文學性,而依賴演員的動作與歌喉,也就是依賴演員的「演技」。 著重「台詞」與著重「動作」,是東、西劇場的最顯著的分野。中國戲劇之所以被視為具有迷惑性與現代化,是由於演員的動作姿態展示了一個視覺世界。 做一個成功的中國舞台演員,並不是件簡單的事。他必須從童年時起即接受嚴格的訓練,直到他學習到相當程度後,才能登場演戲。從舞台經驗中提煉自己的體會力,表現力,他必須做到圓熟的掌握肢體運作,控制自如的嗓音,來表達感情思想。使他所扮演的人物成為視覺中的真實人物。因此,一個中國舞台成功的演員,應當是舞蹈家、歌唱家、戲劇家三者合體的藝術家。 中國舞台演員,實際上,是舞台的主宰。 三、臉譜的藝術真義 在現代最進步的心理學理論,運用於藝術及美學方面的成效,常被表現於現代畫的各派別畫作,現代畫家懂得如何運用這些原理,把人類本質轉化為藝術品。中國戲劇的臉譜,在數百年前,已經這樣做了。 中國舞台演員何時放棄使用「面具」,而採用以顏色塗抹在臉上,作為「臉譜」,已不可考。依常識說,使用面具較之描畫臉譜,應當方便多多,面具只須一隻存放的箱子,演員上場時,隨時取用。臉譜既須攜帶各種色彩油料,畫畫等工具,而且描畫工作,既需技巧,也費時間。 然而中國舞台演員,卻是富有藝術秉賦,而不是機械員。他們放棄面具,採用臉譜,是一種藝術行為。他們認識「戲劇感受」基本上是人性的而不是裝飾的;面具固然也有其藝術價值,但是靜止的,裝飾的,也是削弱人性的,因之,他們只使用之於裝神扮鬼,而不用來刻畫人物。 臉譜既生動又能誇張人性,人的體態面相,原也是人性最忠實的表現,臉部的肌肉,給予線條和圖案,同時也給予生命,這些線條與圖案。無礙於臉部肌肉的運動,睜眼,張嘴,聳鼻,一樣的可以靈活控制,並且強調了人物表情,一切的目的全為演員而設。 具有雄偉,魯莽,勇猛性格的人物造型,穿的是寬大服裝,內襯厚厚的「胖襖」,穿的是厚底靴,動作誇張而渾雄,如果不配上臉譜,其形象是不可想像的。 四、動作的表現力 最具深度的舞台動作是什麼,也許可以說是一系列當有韻律的動作,揉合著所要表達的意念,成為統一性的結構。 動作可能出發於現實生活的表現,也可能是舞蹈型,兩者全可出之於規範化。用手掩目,聳動肩膀,垂首,一種具有韻律與形式的動作,是出發於生活的哭啼表現。戰士表現英勇與自信時,使用一連串的「鷂子翻身」身段,則屬於舞蹈型,在生活中決不會有的,主要的是把各種動作藝術化的連繫起來,交替運用,前一種可屬於生活型,後一種可屬於舞蹈型,前者可能是寫實的,後者可能是抽象的,而演員操作時既不見力竭,也不見勉強。 舞蹈型的動作最容易被人欣賞、接受。「翻筋斗」、「吊毛」、「虎跳」、「搶背」、「旋子」,各種不同的不容易做到的肢體運作,往往使觀眾驚奇激動,如果這些動作僅僅是表現演員能靈活的控制肌肉,運用肢體,而動作本身並不具有目的性的話,那只是種「特技」表演。中國演員往往有種自覺,一種來自藝術本質上的感性與表達性的自覺,能夠把這些動作有目的的使用於刻劃人物性格,及描摹特定情況,達成這項表現任務,也必須具備一定程度的體魄,感性與智力,綜合三者使動作與思想結為一體,才算得是舞蹈藝術而不是特技。 舉例說:「關公走麥城」一劇中,描寫這位英雄在孤立無援的戰場上,做出許多強烈而有力的動作,觀眾好像真實的看到他騎在馬背,在冰上滑行一樣,時起時落的作各種掙扎動作,還有「三岔口」,種種類似特技動作,全運用在黑夜進行打鬥的情況下,一招一式,全有其目的性,無怪法國的劇作家巴羅特Jean Louis Barrault導演莎士比亞劇作,處理戰爭場面時,也採用近乎特技的舞蹈動作,這類動作是富於表演力,暗示性的舞蹈,不能僅以特技目之。 中國舞台肢體動作具有寫實、規範、自由、象徵等特質,中國舞台術語,動作是結合手、眼、身、步法為一體的操作,表演時互相配合,不可分割的。運用的方式則各有不同,例如扮演猴子和豹的動作就絕對不同。人物的動作,基於男女性別,社會身份,家庭背景等的不同,動作因之各異。女性(指青衣型)高貴,貞靜、典雅的情操,純以動作來表現,好像微風中的柳條,輕柔有致,動作的範圍也小,不出身體的周遭,她的「靜趣」,又好像一尊精美的磁像。 五、服裝、道具的功能 中國戲劇的服裝、道具、與人物的結合非常嚴密。服裝代表人物的性別、年齡、身份,甚至性格,全是很鮮明而簡要,令人一望而知的。 演員透過服裝來表現人物的感情,則不是很簡易的操作。水袖的運用就是明顯的例子。甚至屬於頭飾的翎子,也可以運用為表現高傲、英勇、憤怒各種情緒,長鬚和水髮,也有表達情緒的功能。 道具也具同樣的戲劇性表現功能,如囚犯的鎖鍊,在演員工手,便成為表達情緒的工具。扇子的戲劇功能,觀眾更容易發現,很多齣戲全有拿扇子的人物,懂得中國戲的人,決不會認為與劇情季節不符而否定其戲劇功能。馬鞭,船槳,車旗,兵器等道具,更為一般觀眾所熟知。不過,粗心的觀眾,也許沒有理會到服裝、道具與演員的嚴密結合的程度,已達到服裝即演員,演員即服裝的最高舞台藝術法則。 六、西方觀眾最不易接受的音樂 西方觀眾對中國舞台藝術最不易接受的是音樂。中國音樂的結構和西方音樂相異的距離實在太大,剛接觸中國舞台音樂的西方觀眾,簡直不能忍受,甚至認為歌唱類似原始人類在森林中的呼號聲。尤其是武場的鑼、鼓、鐃、鈸的喧囂,刺激聽覺,聽來不適耳。 但是,略為深入的觀察後,即使成見最深的西方觀眾,可以發現這些喧囂的武場樂奏,演員不自然的歌喉,完全與整個劇場相配合,也與整個舞台表演體系相吻合的。 最先,他可以發現生活化的東方劇場不厭嘈雜,有類於鄉村節日演出一樣,以鑼鼓來激動的娛樂情緒,是觀眾所要求的。其次,他會發現這些嘈雜的武場音樂不是沒有他的節奏與韻律,他的節奏與韻律是與舞台動作、歌唱相依相輔,而且有加強戲劇感染力的絕大功能,最後,他可以由之進入另一個視聽世界,那兒,一切全是和諧的進行者,那反自然的喉聲,象徵性的動作,不合人身比例的服裝,嘈雜的音樂,一切反自然的成色中,會有一個超現實的藝術邏輯,從富於民間趣味的劇場中湧現。 當你看到音樂員沒有遮擋的坐在台上,檢場人員出入於舞台搬動道具,你一點也沒有感到破壞了舞台,而認為他們屬於舞台整體結構的一部份,那你真可享受中國劇場的樂趣了。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