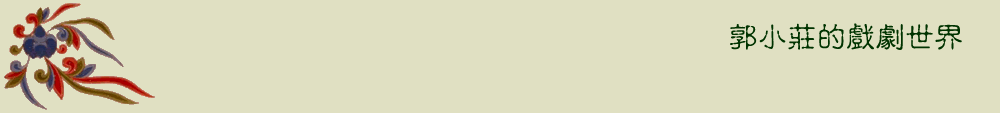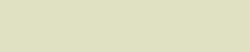| 看俞大綱先生的「王魁負桂英」 |
| 【中國時報/施叔青】 |
| 1972-12-27 |
戲劇是一種綜合的藝術。在東方戲劇裏,中國的平劇包含了多種的藝術(音樂、舞蹈、美術)所組合而成。西方的劇場也同樣地講究舞台上的美術線條、全劇的氣氛、顏色、節奏,以及注重聲、光的效果。在本質上,東西方劇場卻產生不同之點。我們可以說西方的戲劇是「劇作家的劇場」(Playwriter’s Theater),因為劇本是整個戲劇的靈魂。所有的導演、演員、舞台設計家,莫不依附劇本的內容才產生靈感,再求自我表現。構成劇場重心的劇本一不存在,那麼就無所謂戲劇了。同時依照美國戲劇評論家史達克•楊 (Stark Young) 的論調,他以為劇本是劇場中唯一可以流傳下來的,其他如導演、演員、佈景、燈光,終將隨演出之後而消失。五百年後的今天,莎士比亞的劇作依然不朽,一直被當成文學作品來討論便是最好的例子。
反觀中國的平劇,則是一種演員的劇場(Actor's Theater),因為中國戲劇在成戲之前,早已經先有了音樂與舞蹈。隨著長時間的琢磨,這兩種藝術形式已經有了相當的完整的一套表演方法。中國戲劇裏,情節故事的加入,就整個長遠的歷史看來,還是晚近的事。然而戲劇是人的生活的反映,這是誰也無法否認的事實,雖說平劇劇場並沒有忽略了戲劇應植根於生活,然而,平劇音樂、動作對整個戲的形成來說,卻不無喧賓奪主之嫌。中國人是個有歷史傳統癖好的民族。當年一些老伶工把歷代的野史故事拼湊起來,便成了結構鬆散的平劇的劇本。受囿於強烈的道德意識,平劇的思想簡單,主題不外乎報應主義,人物則是一成不變的二分法,這影響了劇本的結構,永遠跳不出因果關係的情節(Cause and effect plot),由於「問題」與「答案」的必然性,西方戲劇中所講求的戲的發展,轉折,以及人物心靈追索的過程,往往不是平劇劇本所關心的。如何在因與果之間填滿這一截空白才被認為是戲的精華。於是平劇的動作往往流於一個平面,是靜止的(static),如何來填滿問題與答案之間的這一段空隙,這工作便落到演員身上,小丑的詼諧,旦角的唱作,以及平劇裏特有的重覆的對白、動作,便在這裏發生了功用。觀眾熟悉了重演不息的歷史故事,他們在一種預知的情況下看戲,可以不必為角色的遭遇而擔心。演員的唱作、身段、台風反而變成了觀眾欣賞的焦點。由於劇場的氣氛,演員的服飾,美術化的動作,觀眾並不溶入戲中,反而是一種疏離,他們採取遠距離的心情來欣賞演員技藝的優劣,甚至由這個來論定整齣戲的好壞。
「王魁負桂英」的作者俞大綱先生,顯然意識到,如果這一代的中國人還因襲傳統編劇的老路,不在劇本上下功夫,那麼平劇這種劇種,無疑地會很快沒落,賸下這套精采絕倫的表演方法,終究也不過像是屏風上的鳳凰,雖然彩色鮮艷,畢竟也是死的。
珍惜平劇這一套完整的風格形式,把它本身的規格當成一種特質,寫出有體溫的,與現代人的感情貼切的劇本,讓平劇不再僵化,反而流著一脈新的血,持續這一個可貴的劇種,似乎是俞先生的抱負。終於,「王魁負桂英」以一個值得喝采的新姿勢出現了。
做為一個劇作家,俞先生掌握了平劇的神髓。那就是東方戲劇裏特有的,以姿態、手勢、生理上的動作來表達內心的感情,這與完全以口述的語言來表現的西方劇場比較,平劇以「動作」來詮釋心理,實在是一種更複雜的藝術。在「王魁負桂英」一劇裏,這種詩劇的美感,全都藉著「動作的語言」呈托出來。俞先生同時也懂得如何精簡濃縮的戲劇情節來套入這些美的動作,他採取了西方的──或者說比較合理的──編劇方法。把平劇裏習見的枝葉橫生,漫無組織的情節,一一鏟除,而改用一種深入劇中人心理的,感覺細膩的手法來編寫平劇的劇本。俞先生大膽地把東、西戲劇的精華溶合在一起,這個近乎完美的組合,使我想到法國前衛戲劇評論家阿陀(Artaud)終其生在他的書裏呼喊著東方劇場的高妙,以及西方戲劇工作者學習東方的必要,如果他仍在世,看到了俞先生這種精妙的結合,該能瞑目了吧。
就戲的結構來分析,「王魁負桂英」正符合「單一情節」(one single plot) 的原則。作者把整個戲濃縮到一個主幹,所有戲裏的發展、危機、衝突、高潮,甚至結尾,都是依附這條主幹而進行。在這裏,作者把戲的焦點集中於桂英身上──他所最喜愛的人物。我們可以說這是個焦桂英的戲。因為劇裏的動作是始於桂英的期待,接下來懸樑自盡,最後找到王魁,令王魁誤傷自己。全劇的過程離不開這個軌跡。就戲劇上的術語來說,這是一種顯而易見的表現方式(physical plot)。除了這條「外在的情節」,還有更重要的「心理的情節」(psychological plot)也就是主人翁焦桂英心理活動的情形,由她執著的癡情,發展到被王魁遺棄後的悲憤,然而又不死心地去探情,這一連串心理的起伏,我們稱之為「心理的情節」。俞先生在這裏,巧妙地把這兩條有形與無形的情節線索綁在一起,另外兩個主要人物王魁、王興,也向著同一方向,造成相輔相成的效果。如此,「王魁負桂英」就成了有跡可尋,結構緊湊的一齣戲了。
關於人物的選擇與安排,俞先生揚棄了平劇裏習見的大堆頭,卻又因太多角色而成累贅的陋習。他以最經濟的手法,把戲放在三個人身上:桂英、王魁、王興。這三個人都有存在的理由,作者摸好了這三個角色的相互作用,由他們之間的衝突矛盾來推動全劇。俞先生讓他所塑造的人物上場都有它的必要性,這種凌越傳統平劇的處理,除了顯示出俞先生懂得好的劇本的編寫方法之外,更讓我們感到,俞先生是太懂得平劇其實是一種詩劇的道理,他要在他的劇本裏強調詩劇的單純的美感。誰能否認戲劇的迷人之處就在於它的Simplicity?
一個古老的主題;屬於精神層次的真情與人世間權勢的衝突。在戲裏,白髮飄飄的老僕王興,以及青樓女子焦桂英,合力呼喊出人類的摯情,以及對索求應有的公道的努力,卻因為他們的微賤,而令他們的呼喊,只不過成了一個淒涼的手勢,也因為這,全劇充滿了悲劇的氛圍。王魁是一個不折不扣的Social Climber,飽讀詩書只不過是做為他往上爬的手段。這個往後應該以身訓人的「狀元公」,他的絕情與勢利,比起青樓女子焦桂英的癡情,以及對感情的維護,是何等辛辣的嘲諷。在這裏,作者除了運用「對比」(Contrast)產生戲劇上的「嘲弄」(Irony)外,也同時點出作者對桂英人格的尊重,這是何等的胸襟!
然而,俞先生太重視焦桂英所提出的精神價值,也因為作者太厚道了,一心想要替被侮辱、被傷殘的弱者伸冤。他的這片心意籠罩了全劇,也因此他把王魁醜化了。作者沒把王魁的苦衷挖深進去,也沒能為王魁週遭環境的矛盾,設身處地的想一想,致使王魁這一角色的刻劃只留於浮面,而未能深入探究王魁內心的糾葛,顯出了人物二分法的痕跡。這樣的處理使得王魁與焦桂英的關係不能平衡,削弱了兩人互相爭持的力量。我們知道,在戲劇上,唯有兩股相等有力的衝突,在勢均力敵的相爭持中,才造成了戲的張力。而不是像王魁與桂英,一強一弱,王魁註定要被觀眾嫌惡唾棄。這種一面倒的現象,還是出於作者太過厚道,他實在無法忍受王魁的薄倖,以致只強調王魁的負心這種人格上的缺失,卻不願意顧及到王魁的苦楚。作者最明顯的用心,是在王魁知道桂英殉情,接下去「情探」一場,他去書齋小坐片刻,為的是「定一定神思,以免見了相府千金,被她看破我的心事」,還狠心自得地吟哦「落花如有恨,墜地也無聲」。相反地,被逼死的桂英還悽惋地前來乞求這個負心人,替他留餘地,以中國女性那種還可以原諒的寬容心懷,試圖拾回昔日的恩愛。王魁這時充分顯出了他知識、地位貴族的優越感。受制於作者爭著公道的聲討聲中,觀眾除了氣憤,顯然被故意醜化的王魁,而感動於桂英這種代表中國深厚的道德情操之外,一點動彈的餘地都沒有。
全劇是由六場戲所串連而成,戲的重量落在後半部。寫一場寄書等於是「序曲」,「訣院」裏托出了桂英的性格與決心。「淒控」與「冥路」兩場戲都是為最後高潮的準備工作。一個極好的伏筆。前三分之二的戲進行節奏緩慢淒美,作者傾力營造氣氛,慢慢地(Build up)(堆砌),在令人屏息的時候,繃緊的弦一下斷了。於是,開始了一場有聲音,有動作,有美的高潮。作者把握住高潮過後,迅速結束全劇的原則。
在這裏,作者由桂英的觀點跳到王魁的觀點(Point of View)。俞先生相信劇作家是全能的。最後一場桂英的魂靈來找王魁,就俞先生的解釋,完全是王魁自己一連串的精神活動。這裏發生的一切完全是以王魁的眼睛所看到的,而將這種意象(Image)以形象的方式來表達,更是舞台戲劇這種媒介(medium)受時、空限制的明證。
俞先生根據「王魁負桂英」的原作,將它寫成一個感人的悲劇。他巧妙的運用了鬼的出現──這的確是平劇舞台的獨步──渲染了那股淒絕美絕的氛圍。然而,在態度上,俞先生安排的鬼魂,並不是傳統平劇中,利用中國人的迷信,假藉另一種超自然的力量,來驚嚇所怨恨的人,以逞其復仇的心意。假借神鬼,實在是一種極為無可奈何的心情。前面俞先生自己澄清桂英的鬼魂出現,是由於王魁的心理作用,何況雖說在理智上,人們拒絕相信鬼神,但是在情感上它卻有說服人相信的可能性。所以,在二十世紀的今天,安排這場鬼的出現,基於某些理由,並不是不合理的。
首先,在「淒控」一景上,我們承認焦桂英懸樑自盡的這一事實,所以接下來「冥路」,桂英扮鬼出現,傾訴她此行一探真情的心懷,接下來,俞先生並不借用「女鬼索命」的俗套,「情探」一場,桂英卸下鬼扮,而以原來面目出現。俞先生把桂英拉到人世間來(如果這一景全是王魁的幻象,這種安排絕對合理),他讓桂英與王魁在同一個世界,這一點很重要。唯有如此,兩人之間的愛恨、糾葛,以及心理的翻騰才是可信的,桂英是以一生命之軀,向王魁淒求控訴,才更有真實感而且有力。如果換上陰陽兩個世界,桂英來討取公道,試探真情的動機就顯得虛飄而荒誕了。俞先生肯定了人的力量,一切以「人」為主。這種態度與執著是可敬可賀的。
做為一個編劇家,俞先生明白戲劇是一種「視覺藝術」,是應該用動作的「顯現」(Show),這可從兩個地方看出來;一是桂英倚門而望的動作,另一個是桂英把筆、硯、書排好,自己坐在一旁,裝做陪王魁讀書。桂英刻骨的相思都借這兩個動作表現出來了。這種由外面形象的舉動,擊入觀眾心裏的,感動力遠比語言的力量要大。另外俞先生也把羅帕這一「道具」(Props)用得極好,它可以是代表愛情的信物,也可以是用來自殺的工具。
至於演出方面,郭小莊的焦桂英有超水準的成績。以一個入世未深的演員來說,和能掌握住焦桂英那份內歛而充滿激情的才能,實在不易。尤其是「看信」一景,在短短時間內,郭小莊捕捉住了幾個全然不同的感受;先是甜蜜,轉為驚詫,再是絕望,最後決定以身殉情,心理的轉折刻劃極深入。飾演王興的哈元章,他的樸實與執著,確實表現出人類的普遍價值。他煽回了中華民國特有的人性。
「王魁負桂英」是個充滿了文人氣息的劇作──其中好詞充塞。單線進行的情節不免使全劇略顯單薄,可喜的是裏面有俞先生深厚的同情心,與縱橫的氣勢做支撐。它是一齣風格特出,純淨淒美的好戲。
讓我們向俞先生敢於以新的觀念,來持續中國戲劇這一戲種所跨出的一步,致最大的敬意。(完)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