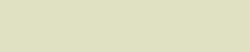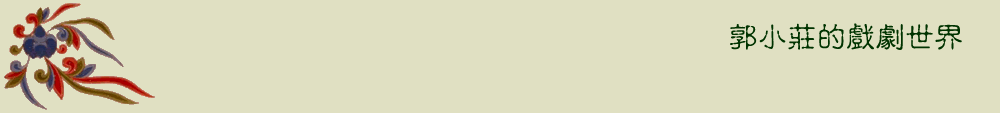
俞大綱先生遺作「王魁負桂英」 俞大綱教授生前,曾編過三齣國劇──王魁負桂英、繡襦記、和楊八妹。 「王魁負桂英」,與其說是最新的戲劇,不如說是最最古老的戲曲。元朝的葉子奇在草木子裏說:『俳優戲文,始於王魁,永嘉人作之。識者曰:若見永嘉人作相,宋將亡。及宋將亡,乃永嘉陳宜中作相。其後,元朝南戲盛行,及當亂,北院本特盛禹,南戲遂絕。』明季的徐文長在「南詞敘錄」裏稱:『南戲始宋光宗朝(約在公元一一九○年),永嘉人作趙貞女,王魁二種實首之,其盛則的南渡,號曰「永嘉雜劇」,又曰「鶻伶聲嗽」。其曲則宋人詞而益以里巷歌謠。』 如此看來,我國的戲劇形成於北宋之末,南宋之初,當時,可能並沒有劇本,直到南宋的中葉,纔有戲文,王魁列於榜首,趙貞女與蔡二郎,亦為一時之選。不但如此,「王魁」之劇,出於永嘉人的手筆,然而,這本「王魁」的戲文,又何以能預言為宋室亡國之兆?據明季陸容菽園雜記載:『嘉興之海鹽,溫州之永嘉,皆有習為倡優者,名曰戲文子弟,……其扮演傳奇,無一事無婦人,無一事不哭,令人聞之,易生悽慘,此盡南宋亡國之音也。』 姑不論其是否為亡國之音,據諸位先賢的著述,宋人有「王魁」的戲文,宋元之間,翻修為「南戲」的「王俊明休書記」,這兩本戲文的內容如何?因其早經散軼,不克悉其本末,但是,約在元初,浙江的省務官尚仲賢,將這篇戲文,翻為北調的元曲,題目是:「海神活取命」,正名作:「王魁負桂英」。另有個正名為:「海神廟王魁負桂英」。 尚仲賢的雜劇,敘王魁落第,無顏重返故里,遊於山東萊州,友輩招遊北市,有女豔絕,共與酌酒,友人贊稱酒乃天之美祿,足下得桂英且飲天祿,實明春登第之佳兆。桂英乘機取下擁項羅巾,請其題詩,王魁提毫立就,詩曰:『謝氏筵中聞雅唱,何人戛玉在簾幃?一聲透過秋空碧,幾片行雲不敢飛。』桂英深慕其才,面告王魁,願為負擔其四時生活所須,但請安心攻讀,於是,結為夫婦,從此之後,王魁朝去暮來。逾年,有求賢之詔,桂英為之籌辦西遊之所需,行前,二人同至州北海神廟,王魁在神前盟曰:「吾與桂英,誓不相負,若生離異,神當殛之。」後,魁唱天下第一,私念科名昭著,而為一娼婦玷辱,尤為嚴君所不容,遂與之絕。王魁大魁之後,桂英以詩賀之,竟不作答,而魁之父已約崔氏為親。及魁授徐州僉判,桂英遣僕持書求見,魁方坐太廳決事,聞而大怒,叱書不受。桂英曰:「魁負我如此,當以死報。」揮刀自刎。魁在南都試院,有人自燭不出者,桂英也。桂英曰:「君負誓渝盟,紿我如此。」魁母召道士馬守素醮之,守素夢至官府,魁與桂英之髮,相繫而立,有人戒曰:「汝知則勿復醮也。」後數日,魁竟死。 據我猜想,尚仲賢可能是以「王魁」和「王俊明休書記」為藍本,依照元人雜劇的規格,翻為北曲,在全劇情節方面,不至有太大的變化,換句話說,永嘉人所撰的「王魁」,就是個感情的劊子手,「王俊明休書記」的休書,就是桂英的死亡判決書。這些在尚仲賢的筆尖下,可能是一成不變,因此,降至明初,最早期的雜劇作家楊文奎,寫下了翻案的雜劇「王魁不負心」,惜其本不傳,就連該劇的題目與正名,亦無蛛絲馬跡可尋,究竟,王魁何以未負桂英? 又經過了一段相當的時間,江蘇松江的王玉峰,又寫了一本為王魁翻案的「焚香記」傳奇。這本四十齣的傳奇,使北曲還為南曲。在傳奇裏,如何為王魁洗刷罪名呢?其首齣「統略」的詞曲「滿庭芳」云:「濟寧王魁,樁萱早喪,弱冠未結姻親,赴禮闈不第,羞澀寓萊城,偶配桂英,新婚後神廟深盟,試神京,鰲頭播占,金壘起奸心。為奪婚不遂,將家書套寫,致桂英自縊亡身,幸神明折證,再得還魂。徐州破賊聞家難,兩下虛驚,種諤統兵,萊陽解寇,重會敘前盟。』詩曰:『辭婚守義王俊民,捐生持節檄(去木字旁)桂英,施奸取禍金曰富,全恩救患種將軍。』按:明清兩朝的傳奇,首齣都有概述全劇情節的詞曲,並題詩四句,似是「雜劇」的題目與正名,亦相當於全劇的提要,藉以補充詞曲之不足。復按:劇中安排的金壘,字「曰富」。 在這齣傳奇裏,王魁的樁萱早喪,使為無父無母的孤兒,當不致為「嚴君所不容」,且去須由「魁之父已約崔氏為親」,更無須由「魁母召道士馬守素醮之」了。 「焚香記」裏,安排了一個富甲全城的金壘,私戀桂英,欲得之為妻而遭峻拒,因在王魁高中之後,套用「荊釵記傳奇」改書的手法,原一如「荊釵記」之唱「一封書」云:『離家後幸安,為卿卿日掛念,科場事幸然占魁,名忝狀元,除授徐州為僉判,特請同臨莫作難,謝公前,致情情,媽媽姨娘可代言。」這封萬金家書,旨在迎春赴任所。「謝公」本是元雜劇中邀王魁遊於風化區的友人,這裏升格而為長輩,以桂英為其繼女。 這一封書,經金壘買通送信的使者,偽造文書,予以盜換,金壘改書時所唱的「玉交枝」是:『王魁具柬附投入,投入程姐粧前,到京身體粗健康,不勞再賜縈牽,幸然一舉做狀元,那韓丞相招贅為姻眷,我既有新婚舊難全,若要改嫁,任從伊便。』 檄(去木字旁)桂英讀了這封休書,並未揮刃自刎,改為投繯自縊而死,藉以保全其屍體,便於還陽。桂英自裁致死之後,魂靈兒飄飄盪盪,飄盪到海王廟,神像之前,哭訴王魁負心背誓,將她遺棄,是「綴白裘」中所載的「陰告」,俞大綱教授改稱「悽控」。全案的經過,由海神爺予以追蹤調查之後,悉為金壘橫刀奪愛,一再逼婚而不擇手段之所致,因而攝其靈魄,處以應得之罪,賜准桂英還魂,重諧舊好。 王玉峰是不是根據「王魁不負心」而改為「焚香記」,把一個同歸於盡的悲劇,一變而為死而復生的喜劇,固不得而知,不過,宋元之間,還有一本「王魁傳奇」,不悉出於何人之筆,傳至明季,全文散軼,僅殘存四支殊稱珍貴的詞曲,特予輯錄於后。 其一「長生道引」:三鼓將傳,誰家長笛頻吹?此景教人怎存濟,神思自覺昏迷,珊瑚枕上,並根同蒂,放嬌癡,恣歡娛,如魚如水,釵橫鬢亂不自持,嬌無力,倩郎扶起。(合唱)我和伊,傚學鴛鴦,共成一對,顯得誰樓上漏聲遲。 其二「熙州三台」:晚來雲淡風清,窗外月兒又明,整頓閣兒新,飲三杯自遣悶情,久聞倩芳館名,猛拚一醉千金,活脫似昭君,行來的便是桂英。 其三「十二嬌」:伊家恁的嬌面,悄如閬苑神仙,終不漾了甜桃去,尋酸棗,再吃添。(合唱)同往聖祠前,雙雙告神天。 其四「泛蘭舟」:鎮日花前酒畔,狂蕩煞迷戀,春闈赴選音傳,恩愛惹離怨,天付因緣,一對少年,爭忍輕散,心事待訴君言。 這四支詞曲,據前賢推斷,可能是宋末或元初的作品,然而,既不見於尚仲賢的「王魁負桂英」,復不見於王玉峰的「焚香記」,幸經明季的詞曲名家沈璟,輯於「南九宮譜」之內,實有珍如片羽之感。不過,在這四支斷簡殘篇的管窺之下,究竟是「王魁負桂英」?抑為「王魁不負心」?則無從分辨了。 總之,王魁的故事,在我國的戲劇來說,是一齣名劇,抗戰期間,客食渝蓉,兩度欣賞川劇的「情探」,就是「活捉王魁」,劇中,小生上唱「月兒高」,敘述在幼年的時候,雙親見背,得焦家之救濟與聯姻,與桂英海誓山盟,金榜高中,在韓相府贅為東床快婿,懷念桂英,感慨萬千,旦腳率鬼卒上,鬼頭欲捉王魁,桂英為之求情,且待試探其情意後,再做決定,是以豔妝而晤王魁,細訴前情,更唱「鎖南枝」,敘述別後的相思,然而,一再懇其收留,甚至願意作妾為奴,王魁不但不允,反而怒摑桂英,至此,桂英變臉,眾鬼卒同上,活捉王魁。 元雜劇以王魁深恐娼門玷辱而棄桂英,桂英揮刀自刎而陰捉王魁。明傳奇以王魁入贅相府而拒桂英,桂英懸樑自縊,活捉王魁。且以桂英姓檄(去木字旁),川劇一如傳奇,然桂英姓焦,且在陰告之後,海神訴諸五殿閻羅,閻羅遣鬼卒隨桂英同去,活捉王魁。這是各種劇本之異同。 俞大綱教授生前,曾以其所著「王魁負桂英」之劇本見賜,細讀之下,係以「焚香記」為底本。參考川劇,再翻版而使王魁負桂英,排場、詞藻,均較雜劇與傳奇為勝,且以「京韻大鼓」開場,敘述前情,簡單明瞭,別開生面。 「王魁負桂英」是名旦郭小莊所獨有的本錢,據說,郭小莊拿到這個劇本,曾費盡苦心,琢磨鑽研,唱腔、身段、表情,均曾一再修訂,尤以「活捉」一場,有「水滸記」與「紅梅閣」等,演之於前,在觀眾的心理上,已先入為主,既不能抄襲剽竊,惟有求新求變,這一切,在郭小莊的努力上,獲得了無數的佳評與盈耳的掌聲,眾口鑠金,尤其是最近在文化學院的畢業演出,演出之前,因車禍受傷而留院醫療數日,回家休養期中,尤感昏昏沈沈,然其演出的情形,極為認真,一絲不苟,值得讚譽。 總之,從「王俊明休書記」到「海神廟王魁負桂英」,再從「王魁不負心」到「焚香記」,以迄時下皮簧演奏的「王魁負桂英」,戲劇的故事,並沒有強烈的變化,但在劇本與演出上,卻有著相當的進步。准此而論,戲劇應求變求新,迎合時代的需求,僅以清季中葉盛行的「焚香記」而言,雖是四十齣的全本,只演「陽告」「陰告」等數折,也都是全劇的精華。俞大綱先生改以「京韻大鼓」而述說前情,刪除所謂冗場,簡捷有力,確乎是值得推崇而超俗的手法。 |